嗯,我沒什麼可失去的了。
2022-06-16 13:51:48 492 admin

上一份工作做了许久,内心并不非常喜欢,想要辞职,但碍着疫情缘故,瞻前顾后两三年,始终不能下决心。
身边有位家乡在温州的朋友,行事风格飒爽果决,大学毕业后勇敢北上,创自己的业。我羡慕极了:“你比我更像传统印象里的北方人,我怎么这么不爽快。”她大笑:“是啊,不明白你到底在害怕什么,明明家就在这里,有的是后路可退。”
我很好奇,问她为何离开温州,留在家里不好吗?她愣了一下,然后理所当然地说:“我们温州人,就是这样的,我爷爷说温州以前什么都没有,所以也没什么可失去的,只管往外闯就好了,大家都是这样,往外走,出去拼,拼出自己的天地。”

所以,其实这位温州的朋友跟我说的那句“家就在这里,有的是后路可退”,背后藏着的,是一句“越是习惯了拥有,越就没办法放手。”
朋友跟我讲起小时候她爷爷给她讲的故事。以前的温州,三面环山一面朝海,没水没电,没柴没米,更没有什么国企工厂,干旱时连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,老辈人穷怕了,逼出一股狠劲往外闯,反正家里一无所有,只剩一条命,就拼了命去挣一口饭吃。

爷爷生了五个孩子,一个大女儿,四个儿子,没有一个留在身边,全部顺着潮汐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,唯一的女儿是最远的那个,在巴黎,做餐饮生意,开了自己的店铺后,又把家里另外两个女眷也带了过去。
没有一个人觉得离家太远会怎么样,即使现在家里状况已经好了太多,但似乎老一辈的那股孤注一掷的拼劲儿已经留在了血液里,家族里的每个人,没有一个会沉溺于眼前的拥有,让自己停下脚步。什么安于现状,什么学会知足,这些东西,极少出现在温州年轻人的字典里。

我羡慕这位朋友做事果决爽利,无所畏惧,或许恰是因为她认定自己原本一无所有,没有拥有也就不怕失去,所以勇敢。而我在意的太多,害怕动荡,一点点失去就会让我耿耿于怀,因此也就越来越胆怯,越来越懦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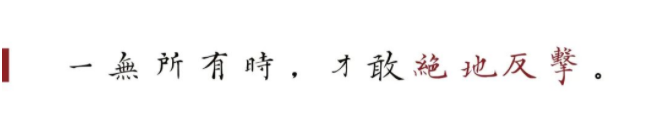
可是人啊,能够做到怀着一无所有的心情,去突破日复一日惯常的生活,实在太难了,常常只有逼到绝路的人,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什么可失去时,反而敢于跟生活决一死战,从无望的逼仄中杀出一条生路。
想起那部招惹了许多眼泪的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里,五岁时就罹患癌症,但肆意明媚、古灵精怪的少女马小远。
与青春叛逆期确诊癌症的“丧气少年”韦一航面对世界的怨气截然相反,马小远从小就大把大把的吃药,几乎幼时就已经懂得“活着就已经很难”这件事了。在那样绝望的处境中艰难长大的马小远,反而早早地学会抓住每一丝“希望”的气息,珍惜每一个崭新的日子,热烈而耀眼的活着。

每一个“习惯”了与癌症相处的病患,大约都能体会马小远这种肆意欢乐的生活哲学。电影里的“病友群”“互助会”也绝非杜撰,而是真实地存在于各个城市的角落里。
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人,或许会认为这些群体的交流常常是困苦绝望的,但事实上恰恰相反,在这里,你很少会看到怨天尤人和哭天抢地,反而更多是热情积极的互相鼓励,对每一次小小的指标恢复给予彼此最真挚的祝福。
因为已经被夺走了太多,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,所以,哪怕肿瘤已经膨胀到几乎挤占了全部的生活空间,也仍旧要在与病魔相争夺下的每一秒钟,快乐地活着。

那些令病魔节节败退,比“医生判下的死刑”多活几年的故事,不是神话,而是最蓬勃顽强的生命力绝地反击的真实。那些“失去健康后,就真的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”人们,反而比大多数人都更懂得抓住每一刻尚未流逝的生命活力,去相信希望,去努力快乐,去珍惜幸福。

或许,看过马小远的故事之后,我们可以试着回答亚里士多德在《伦理学》中提出的那个古老的问题: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?
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会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,但无论哪种答案,一定都暗含着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观照。当你感到终日郁郁、感到踌躇不前、感到漫长的不甘无法破解时,或许可以怀抱着“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”的心情,去顶撞一下生活,把日复一日的循环撞出一个破口,撞出一个新的局面,撞出一种别样的火花。

前些天,从遥远的老同学那里收到一则久违的,令人振奋的消息。
她原本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,标准996,累到恍惚,却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。家里催她结婚,有那么两年,她的周末几乎被各式各样的相亲塞满了。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她父亲对她大喊“你究竟有什么不满的?看看你现在的样子,有人要你就不错了。”
来自至亲之人的否定,让她在极其痛苦之中做了一个决定,离开家,离开所有熟悉的领域,离开现在的生活,去澳洲,重新开始。
“我三十岁,没地位,没存款,没家庭,没倚靠,青春到了尾巴,没什么可失去的了——但我终于自由了,我要用这珍贵的自由,给我自己新生。”

从朋友圈里断断续续拼凑她的经历,知道她这几年先是上学,晚上打工做兼职,周末带着小相机出门拍视频,做vlog博主。前段时间,她告诉我,功夫不负有心人,她终于赢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。
与旁边的同事聊起这个故事,同事笑说,她并没有真的一无所有啊,她至少有申请学校的资格,有出国的基本能力。但仔细想想,究竟到什么境地才算是“再也没有可失去”呢?失去所有存折里的钱,居住的房子,爱我们的人,甚至我们的生命吗?
而我们又真的可以确定,眼前的一切,都是我们实实在在拥有的,可控的,永远不会离开的吗?我们心甘情愿地待在原地,究竟是因为我们欢欣、喜悦、感到生命的爱与价值,还是因为我们胆怯、犹豫、患得患失?

或许,这才是我那位温州朋友的潜意识吧,在我看来,她绝非一无所有,但她只是不认定那些拥有是“不变”的,与其患得患失手中的一切,她更想要放开那些,专注把握住此时此刻的时间。
无论走到什么境地,我们都可以确定的,就是此时此刻的时间,我们最该做的,或许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时间里,去拥抱爱的人,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,完成自己喜欢的人生吧。
毕竟,赤条条来这世上一趟,原本就没什么可失去的,不是吗?

